近日,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理事长徐真华教授领衔主译的《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由深圳出版社正式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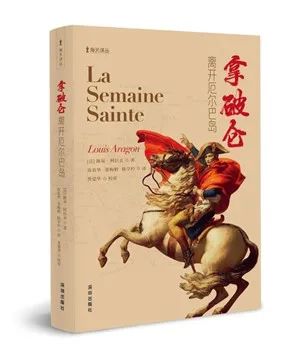
【法】路易·阿拉贡 /著
徐真华、麦梅娟、陈学吟 /译
黄建华 /校审
原著作者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 1897—1982),是法国著名作家,超现实主义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法兰西民族诗人”“列宁和平奖”获得者,布拉格大学“荣誉博士”。曾任《法兰西文学报》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断肠集》《埃尔莎的眼睛》《蜡人馆》等;小说《法国人的屈辱和伟大》《现实世界》等;散文集《巴黎的乡人》《共产党人》;文艺理论集《司汤达之光》《论诗》等。《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是阿拉贡的历史小说代表作。
下文是徐真华教授撰写的译著序
《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译序
徐真华 / 文
1815年3月下旬,拿破仑逃离位于地中海的流放地厄尔巴岛。从登陆马赛到重返杜伊勒利宫,拿破仑的复出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皇帝一枪未发,长驱直入,所到之处民众欢呼“皇帝万岁”,身着波旁王朝军服的旧部纷纷归顺,惊恐万状的路易十八国王仓皇出逃,拿破仑宣布恢复帝国。欧洲封建君主诸国迅速组建第七次反法联盟,对抗拿破仑对欧洲的威胁。拿破仑,这位身材矮小的巨人再一次站到了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最前列,为法兰西“百日帝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01
历史回望:复辟与反复辟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 1897—1982)创作的长篇小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爬梳剔抉的正是这一段初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腐朽的波旁复辟王朝反复较量的历史。让我们随着阿拉贡的所思所言所构想,重温那一幅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
为逼使俄罗斯退出欧洲君主联盟组织的反法战争,恢复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统率60万大军远征俄罗斯。然而,征俄战争以法国的惨败告终。英、俄、普鲁士、奥地利等国的封建君主们迅速成立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年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1879年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室在联军刺刀的保护下重返首都,路易十八恢复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然而,经历了大革命洗礼的法国民众并不认可复辟王朝的倒行逆施。路易十八治国无方,经济每况愈下,通货膨胀之下,农民和工人的生活陷入困境。而王公贵族们的特权则变本加厉,更趋膨胀,民众和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在积累和蔓延。
拿破仑于1814年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一直在寻找机会重返法国。1815年3月20日,他带着他在岛上训练的上千名士兵,乘船逃离厄尔巴岛。不幸的是,他的逃亡信息被英国皇家海军的霍拉肖·纳尔逊将军截获,拿破仑的船队在法国土伦附近的儒昂港遭英国皇家海军拦截。拿破仑侥幸逃脱,船队最终在马赛南部20公里处的昂蒂布成功靠岸。闻信而来的当地民众对皇帝表示热烈欢迎,民众的热情鼓舞了皇帝的斗志。他一路向北,于3月26日进入巴黎,大批已归顺波旁王朝的高级将领,一如内伊元帅,纷纷率部反正,宣布脱离复辟王朝,服从皇帝的指挥。翌日,拿破仑发布宣言,号召民众拔掉那早已被抛弃了的百合花旗,把三色国旗高高举起。路易十八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逃往比利时。
4月1日,拿破仑在法国参议院重申自己的皇帝地位,并迅速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政治上,他承诺进行广泛的民主改革,包括取消封建爵位,没收流亡贵族的庄园,解散王家卫队,释放政治犯,恢复被流放者的公民权利等,以获取民众对帝国的支持。军事上,为对抗欧洲反法联盟,他试图重建法兰西军队。但是,由于财力不足,皇帝的军队无论从规模、装备,还是在战斗力方面都已远非昔比。经济上,他发布《法朗堡宣言》,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国内关卡;取消封建地租和一切封建义务;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事婚姻;恢复公民对土地的占有权。然而这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的重大改革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重振他的帝国梦。
拿破仑重返巴黎令欧洲的封建君主们惊恐不已,他们旋即组建了第七次反法联盟。3月13日,8个联盟国签署宣言,在“保卫和平”的借口下,决定每个成员国出兵15万,抵御拿破仑的军事威胁。1815年6月8日,拿破仑指挥军队与以英国、普鲁士为首的反法联军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决战,再遭败绩。兵败滑铁卢标志着拿破仑军事生涯的终结,也使他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并最终决定了拿破仑及其帝国的命运。在欧洲反法联盟的逼迫之下,拿破仑于6月22日宣布第二次退位,并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直至1821年逝世。
波旁王朝再次复辟。
从表面上看,拿破仑的失败是军事的失败,施瓦岑贝格(奥地利亲王)通过阿尔萨斯进入法国,贝尔纳多特(瑞典王储)经比利时,威灵顿(英国陆军元帅)经比利牛斯山,布吕歇尔(普鲁士元帅)从比利时进入巴黎,跟在他后面的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同盟军有现役军人35万人,预备役65万人,这道雪崩一般的百万大军滚滚涌向几乎不设防的法国。
但是军事胜负的背后永远都是民心所向的裁量。“在延续了二十五年的革命战争和皇帝的战争之后,法国像干渴的垂死之人渴求清水一样地渴望和平。老人们在金字塔的沙漠中长眠,中年人在俄国的雪地里长眠,青年人在莱比钖的沼泽地长眠;只剩下儿童和妇女在地里耕种。‘没有牛拉犁,也可以用铁锹耕地嘛。’内政部大臣安慰道。儿童们耕地,倒下的不是麦穗,而是儿童们自己,这血红色的收成。”
02
火枪手泰奥多尔的精神蜕变
《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描绘了1815年春“百日帝国”的风云变幻,描绘了一个充满私欲、背叛、傲慢、偏见、谎言,也充满思想、探索和变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论是草根百姓还是军官士兵,抑或是王公贵族都承受着岁月的煎熬、生活的磨难、死亡的威胁、道德的诘难和灵魂的拷问。
内伊元帅率领波旁王朝大军投诚的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炸得路易十八心惊胆战,信心全失。惶惶不可终日的国王陛下匆忙带着王室成员和近臣侍从,在庞大的御林军队伍护送下,冒着复活节前夕的凄风苦雨,向比利时边境艰难跋涉。路易十八的火枪手、画家、青年军官泰奥多尔就在这一支逃亡大军中,他目睹了帝国连年征战给草根百姓造成的苦难,贵族统治给劳苦大众带来的不幸,以及向往共和、渴望温饱、工作、自由,但在共同的利益和一致的目标面前却难以统一意志,团结抗争的民众。
在阿拉贡笔下,各色人等不再是戴着单一面具的芸芸众生,而是一个个表情复杂、内心丰富的多面体,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得到了细致入微的铺陈。逃亡大军在风雨中挣扎,饥饿、寒冷、疲劳、绝望折磨着每一个人。路易十八优柔寡断,反复无常,指挥失态;将帅们矛盾困惑,心怀鬼胎,举棋不定。泰奥多尔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在风雨和彷徨无助中寻思着自己的出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与他们不是同路人,他只是被时势裹挟着,卷进了这一支跟随着国王逃难的队伍。眼见路易十八和他的王朝气数已尽,可国王还念念不忘于他的饕餮铺张;王公大臣们还蝇营狗苟于自己的情妇和金币;见风使舵的将军元帅们盘算着如何在保皇阵营与共和阵营之间选边站队;家世显赫的御林军军官国难当头仍不忘寻欢作乐,任意蹂躏外省少女……这些狼藉不堪的人和事随着流亡大军,沿圣德尼、博韦、阿布里索、贝蒂纳、圣波勒等地一路向北,在省城府衙,在农庄古堡,在葡萄园、铁匠铺,在酒肆杂货店一一上演。阿拉贡用他独特的语言和细腻的叙事风格把闻风丧胆的波旁王室,把丑态百出的保皇贵族,把国王、黎塞留公爵、马尔蒙元帅出逃时的种种窘状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作者亦以豪放、生动的笔触展现了泰奥多尔由彷徨到省悟,重新思考战争的价值、和平的意义、民众的出路、国家的命运、信仰的价值取向以及生活与艺术的内心世界。
1789年7月,震惊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权宣言》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冲破了数百年封建君主制统治的桎梏。但是共和政体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政治改革无助于缓和动荡不安的政局。这一复杂多变的形势把拿破仑推上了法兰西政治、军事舞台的中心。1804年,拿破仑在雾月政变后称帝,建立第一帝国。皇帝继承、保卫并发展了大革命精神,推动社会、法治、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暂时制止了混乱的政局。他亲率大军征战欧洲各国,与妄图扑灭法国大革命的君主国反法盟军进行了殊死的会战。恩格斯称他为“真正的伟大的波拿马”,认为他是欧洲“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者。”
从1804年至1814年的十年间,拿破仑为巩固帝国的地位,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先后与欧洲封建列强打了一系列硬仗,连年征战严重破坏了法国的经济生态,重大的人员及物资损失使得民众的生产生活陷入困境,国内的阶级矛盾在激化,国际的邦交关系进一步孤立。这一切加速了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在青年军官、火枪手泰奥多尔眼里,拿破仑从一名出身卑微的普通士兵逆袭成为左右欧洲政治风云的大国统帅,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这是他从皇帝的政治主张与无以伦比的军功中得出的结论。作为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法国民法典》,打造了自由的共和体制。可是皇帝的视野远远超越了法兰西的高山湖海,超越了19世纪的时空:“我最伟大的思想之一是集合、联合各个民族,这些民族在地理上是统一的,但是被革命和政治分开、切割开来……
我想要把所有单一的民族汇集成为一个国家的躯体。”他真正的理想是建立“欧洲联盟”。拿破仑似乎是一位睿智的预言家,今天欧盟的蓝图似乎早在200年前拿破仑的脑子里就开始酝酿。他是“不同于他人的造物”(斯塔尔夫人语),他是“一个为时过早的世界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他不是自己时代的同时代人,而是无限遥远过去的同时代人—在那个时代,当时‘整个大地只有一种语文和一种语言’,统一的人类;或者是无限遥远未来的同时代人,到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羊群,一位牧羊人’。他似乎是另外一种创世的造物;他太古老,或者太新颖;属于洪水之前或者属于启示录时代。”
战争的硝烟破灭了君主制的幻想,帝制的梦想也成了一个美好的泡影。阿拉贡似乎赋予了泰奥多尔一个全新的视角,一种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他开始反思皇帝的专制独裁与警察统治!开始诘问无休止的对外征战是否是帝国的最佳选择,开始质疑皇帝的复出是否会给苦难的民众带来和平与幸福。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让人绝望,皇帝的穷兵黩武,同样让人看不到出路。对皇帝的盲目崇拜开始动摇,泰奥多尔不再纠结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政治立场。
在跟随波旁王朝败军逃亡途中,他有太多机会接触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目睹矿工、马车夫、泥水匠、纺织工、铁匠、乞丐、无产者、失地农民的悲惨生活。而在社会上层,挥霍无度的王公贵族们一个个穷奢极侈,纸醉金迷。惊人的贫富对立使他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意识的觉醒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勤王的热情,他不愿意做那个旧制度的殉葬者。新的思维方式使他放弃了对波旁王朝的幻想,也不再相信皇帝的征战是为了拯救法兰西的漂亮口号。这两派政治势力都不是苦难民众的救世主。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坚决地脱离了这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冲突,决心与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用自己的画笔去表现、去呐喊、去声张正义。
03
文学家的哲思与阿拉贡的超越
泰奥多尔的精神嬗变又何尝不是阿拉贡本人的精神嬗变?作为法国共产党的资深党员,他于1927年加入法共,积极投身党的事业。他曾当选法共中央委员,由20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入道,后投身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德国法西斯入侵期间,作为“抵抗文学”的旗手,他用文学创作讴歌正义,鞭挞纳粹暴行;战后他曾多次访问苏联,赞颂苏维埃的建设成就。然而,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令他无法理解,痛心不已。从此他似乎明白了许多道理,不再拘泥于二元对立的政治逻辑,不再固执于非此即彼的绝对选择。他借泰奥多尔之口,诉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只为把艺术奉献给至高无上的人民,那是艺术家心灵的神圣归宿。
《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于1958年在法国出版,从时间节点上推论,这本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共产党党内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痛苦与失望。
毫无疑问,阿拉贡在19世纪初“百日帝国”的兴衰历史中注入了一名20世纪中叶的现代人的哲学思考。波旁王朝只是那个苟延残喘的旧制度的代表,它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而打着革命旗号的拿破仑同样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帝国连年征战使法兰西的经济到了破产边缘,民众已经开始为食不果腹的面包走上巴黎街头。泰奥多尔力图超脱于这两个利益集团之上,从泰奥多尔身上,我们看到了阿拉贡的影子。他知道一定有一个更神圣的群体,一定有一种更崇高的利益需要他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他知道,泰奥多尔也知道,改变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不是战争,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对立关系的也不是拿破仑的铁腕与强权,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机器……索姆省有多少台勒尼纺纱机?这不只关乎尼绒或棉花……还涉及煤、焦炭、蒸汽……人们了解在矿山和冶炼厂发生的变革吗?机器带来了什么?机器改变了什么?它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改变了人自身……从前我们恐怕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对人的关心不够。要决定未来,不能只懂得驾驭军队。”
这是前国民公会议员儒贝尔对一直被帝国忽略的国内产业情势的分析。阿拉贡借儒贝尔之口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推动法兰西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是什么?成功路径又在哪里?1789年大革命后,欧洲大陆工业革命的勃兴使人们对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认识产生了颠覆性变化。儒贝尔明白,泰奥多尔也终于明白:唯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纠正革命发展的方向,才能推动社会结构的合理变革,才能完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
泰奥多尔思想的拐点由此而发生。“三色帽徽或白色帽徽!”泰奥多尔喊道,“这就是您给我提供的全部选择?如果帝国的国旗今天主要意味着军队,而不是警察,那是因为军队不是人民的军队,那是波拿巴的统治工具!不错,断头台已经从广场上消失了,但他们把年轻人编入军队,把他们派往欧洲各地充当宪兵……”“这就是您给我的全部选择?”这振聋发聩的惊天之问、阿拉贡之问、泰奥多尔之问预示着主人公从精神层面超越二元对立绝对思维模式的巨大转变。
早在1956年,阿拉贡发表诗集《未完成的小说》,写下了《在新桥上》的著名诗篇,在略带哀伤的气韵中,阿拉贡对自己年轻时的“形象”进行了真诚的反思,力图与那个曾经迷惘、曾经轻狂、曾经幼稚、曾经偏执、曾经虚度年华的“旧我”作一个精神上的切割。
从《未完成的小说》到《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阿拉贡开始书写“自我”,一个不再狂热、不再忿懑、不再盲目自信的“自我”,一个突破现状,摆脱困境的自我。是的,人无法改变过去,但是总可以设计自己的未来。每个人都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
徐真华
2023年12月于绍兴鉴湖

